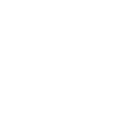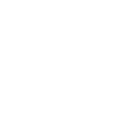乐鱼体育,LEYU乐鱼体育官方网站,乐鱼体育靠谱吗,乐鱼体育app,乐鱼体育官网,leyu乐鱼体育,乐鱼体育入口,乐鱼体育官方,乐鱼leyu官网登录APP,乐鱼后台,乐鱼体育网址,乐鱼体育官方网站,乐鱼体育注册

新时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面对、书写这些巨变是新时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对当代作家提出了更高要求。张丽军的《重新从乡村出发》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梳理了乡村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并在从古至今的文学脉络中阐明了乡村文化之于中国的独特意义。他指出“以乡村为核心的千年乡土根性文化”在21世纪面临着“新危机”,因而提出了“创造新乡村”的主张,包括重构新时代乡村自然之魅、书写新时代乡村人文之史、接续新时代乡村伦理之善等具体意见。面对“乡村将向何处去?乡村一定会消逝吗?”这一现代化、工业化在新世纪中国所带来的新问题,作者不仅在知识领域上下求索,而且融入了个人深切的生命体验,以颇富情感色彩的经验细节与丰富广博的文学底蕴,最终提炼、确认了个人的知识立场:“以文学保卫乡村”。但作者在这里的“保卫乡村”并不是保守主义式的一成不变,而是在人类文明史的整体视野中重新思考乡村文化之于中国、人类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认变什么、怎么变的问题。作者的思考深刻、恳切、真挚,对于新时代文学的乡村书写颇具启发性。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一步加速,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农民的数量。中国在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众多农民也从乡村走向了城市。乡村呈现空心化、荒漠化、老龄化而日渐衰落。留守乡村的农民已经从原来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逐渐走向了现代农业。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型现代农耕机具取代了人力、畜力,从整体上建构起中国式的现代农业技术装备体系和现代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一些村庄在现代化力量之下已经消逝,而数量众多的乡村正处于衰落或渐趋消逝之中。对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乡村将向何处去?乡村一定会消逝吗?如果不消逝,乡村的未来在哪里?乡村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征程中、在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史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不解决乡村的历史定位,不阐述清楚乡村之于人类文明文化的未来价值意义,我们就无法分析和论述乡土文学的未来及其意义价值问题。
事实上,乡村的衰落及其消逝,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且是人类现代化的全球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思考和阐述中国乡村未来命运和价值问题,就有了一种更深层、更辽阔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中国乡村之于中国文化、文学,的确具有一种中国式乡村审美、中国式乡村情感、中国式乡村哲学世界观的独特意义价值。这需要我们以一种更长远的大历史视野来审视和思考中国乡村,在探寻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价值的同时,书写具有新时代中国山乡巨变特征的乡土文学,来传承、转化和建构一种独特的中国乡村哲学美学,打造具有乡愁内涵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而这正是保卫乡村、书写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使命与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以一个个乡村为据点聚族而居,星罗棋布,不断交往融合,构建出了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华文明。在每一个乡村聚居的大大小小族群,以血脉、乡村空间、地域文化等为基点,构成文化认同与心灵皈依的物质、精神基础。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就是以乡村为基点和本位、以家族血脉文化传承为核心,进而延展为国家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乡村地域空间的差异性,构成丰富多彩而又互相包容的地方文化。而摇曳多姿的各地风土、语言、民俗、文学构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互补性。各个地域文化内部的融合交往,创造出了生生不息的原生动力和多维发展的精神内驱力,更是形成了求大同存小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式哲学美学,在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留下深刻的精神印记。
以乡村为审美基点的中国古代文学,从乡村出发,扩展为一种关于故乡的精神原乡美学和浓得化不开的文化心理情感结构。古老的文学经典《诗经》不仅有关于农民在乡村山林稼穑、狩猎等生产场景的描绘,而且展现了乡村世界中的不公,发出了劳苦大众对不劳而获的控诉和对正义美好生活的向往。“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诗经》还有一些诗歌写出了对山川大地、乡土家园的描绘和精神祈愿。“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屈原在《离骚》中的这句话,在种植各种名贵花草的田园中,给予了诗人对理想社会、诗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楚辞·九辩》中的“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则表达出了对乡村田园荒芜的深深忧思。显然,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来自农业文明的乡村田园文化是诗人思想认知和审美书写的逻辑基点,即从乡村、田园、农事和大地出发的生命体验和叙述逻辑。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汉代《古诗十九首》以乡村故土为生命情感与审美基点的诗歌,已经出现了浓郁的“故乡情结”,有了离乡的“故乡情结”的“游子”形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的《七哀诗》写尽了战乱之于乡村农民的巨大灾难,因而发出了“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的对“乐土”的理想乡村的呼唤。“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魏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建构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村,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所心仪的精神乐园,体现为一种对大同世界、乌托邦梦想的精神建构。“桃花源”也成为之后历代中国文人对理想乡村的代名词。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呈现了戏剧与中国文化的民间教化及其文化心理认同的深层联系,而诗中的“赵家庄”为代表的广大乡村就是儒家文化在中国民间传播链条的审美基点。笔者小时候在村里听老一辈人讲述杨家将、呼家将、三国演义,在乡村集市上听民间鼓书艺人讲岳飞传、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薛仁贵与樊梨花的故事,幼小的心灵被杨家的满门忠烈、岳飞的精忠报国、穆桂英的美丽勇敢、诸葛亮的超人智慧与鞠躬尽瘁的精神所感动不已。天理、忠孝、节烈、仁义礼智信等具有根性意义的中国文化就借助于戏剧等民间文艺形式深深扎根于广袤的乡村大地,在乡村文化空间里千年流传,构成一种传承千年的中国乡村根性文化血脉。
事实上,中国儒家文化与民间文化正是在乡村空间里通过文学艺术而有机融合起来。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乡村获得了生动阐释和鲜活流动,不断绵延、拓展,构建了以宗族为根、文化为脉、仁义为本、忠孝为核、尽善尽美、由家及国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家国忠孝仁义文化观,进而凝练为以乡村精神为内核的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而乡村无疑是家庭、宗族、国家、故乡、根脉的最初出发之地和最终归依之地,是中国乡村根性文化的精神基点所在。
鲁迅的小说《故乡》奠定了一种现代色调的乡村悲凉美学。“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故乡》开篇的话语,一开始就令人置身于无边荒凉的冷飕飕语境之中。那个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给予远方游子无限温暖和无限憧憬的“故乡”,已经在工业文明的新语境中成为“萧索的荒村”。即使在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中,乡村虽然还有着无限的美景,但已是“最后的挽歌”了。《边城》中的翠翠的情感世界已有了无法缝补的裂痕。
中国乡村的未来在哪里?翠翠的未来命运如何?翠翠如何把握未来?沈从文在《萧萧》中有过一种可能性的暗示。乡土世界毕竟是变了,有了“女学生”这一在乡下人看来古怪可笑的“事物”,“爷爷”故意取笑童养媳萧萧。萧萧从原来的到渐渐喜欢上了“自由”的“女学生”。而现实是残酷的,“萧萧”依然重复着“童养媳”的命运,但是沈从文已经昭示了乡村世界中的新女性、新道路的可能性。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直接描绘了一种“革命的空气”在乡村里的传播。叶紫的《星》描写了一位从封建礼教压迫中获得挣脱、积极投身革命的乡村女性“梅春姐”。在大革命的时代氛围下,梅春姐从翠翠、萧萧的被压迫的传统女性命运中获得解放,进而成为解放其他被压迫者的新女性和革命者。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梅春姐的解放之路也遭遇了挫折,出狱后被迫重新回到了旧家庭,再次开始新的出走与反抗。显然,没有社会的解放,女性的解放是难以独自实现、获得保障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则从正面阐释了这一道理。正是因为有了新建立的革命新政府的保障,刘家峧村的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才迎来了根本性转机,得到了新革命政府的支持,有了不同于以往乡村恋爱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20世纪中国革命是以乡村为基点,从乡村出发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提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没有农村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就难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有了从农村出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指导,才开启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现代革命道路。
而在文学和革命之外,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找中国乡村的变革及其未来命运。叶圣陶在长篇小说《倪焕之》中指出师范教育把农村孩子培养为城市人的教育弊病,认为中国师范教育要以乡村为教育的出发点和目标,以培养有文化的乡村青年来建设现代意义的新乡村。而真正推进这一教育理念的是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因为抗战爆发等因素,这些乡村建设实践遭遇了挫折,但是其情怀、理念、思维方式和社会实践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以及民办老师、赤脚医生、乡村技术员等一系列新举措的实施,新中国的乡村建设从整体上医治了晏阳初所指出的旧中国乡村存在的愚、穷、弱、私等病症。这在新中国初期的中国乡土文学中得到了大量审美呈现。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李准、王汶石、郭澄清、刘澍德等众多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里边塑造了众多社会主义乡村建设者的形象和对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的美好理想图景。
与此同时,乡村也再次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审美书写的重心,散发出无比生动的时代光辉,出现了高晓声、何士光、王润滋、路遥、贾平凹、张炜、刘玉堂等一大批名家名作。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不仅摆脱了他个人背负的经济负担,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走出了数代农民的生存困境。鲁迅《故乡》中“我”回乡是为了与故乡告别,不仅开启了一个现代乡村的文学书写模式,而且开启了从乡村到世界上去的叙事空间。但是,真正意义的大规模走出乡村到城市乃至世界的却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那里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书写。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翻阅画报中的高楼、飞机等现代新事物,已经有了禁锢不住的走出乡村寻找现代生活的生命冲动。《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不仅延续了高加林的现代梦想,而且以独立主体的精神人格获得了基于平等、尊重基础上的现代爱情,走向了现代新生活的深处,获得一代代乡土中国青年的喜爱,成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经典。这无疑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高峰,也是乡土中国青年形象建构的精神高峰。而此后随着“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村、农业、农民陷入了新的危机之中。
如果说20世纪末的“三农危机”,依然是基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峙与冲突的危机,到了21世纪,随着人工智能的大发展,城市化、高科技化、产业化,万物互联互通、无所不在的高科技与资本力量,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言的科技主宰的“技术框架”。21世纪中国乡村出现了新的危机,乡村空心化、荒漠化、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一些乡村在合村并居运动中已经消逝,那些没有消逝的村庄也在人工智能技术新浪潮中岌岌可危。一种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乡村危机,正在加速到来。也许,明天,后天,我们从小长大的熟悉的村庄可能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事实上,这种乡村危机绝不仅仅是中国乡村的危机,而是整个地球上人类所有村庄所面临的危机。当代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和新锐摄影师、街头艺术家JR联合执导的电影《脸庞,村庄》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呈现了被废弃的农村、被弃置的矿山和处于被遗忘角落的乡村农民、挤奶工、邮递员、流浪汉形象。镜头所到之处满目荒芜,了无生机,触目惊心。2022年上映的西班牙电影《阿尔卡拉斯》一开始就出现的巨大挖掘机始终是桃园消除不了的威胁,随之而来的在桃园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代表了要驱逐桃园农民、变土地为太阳能产业的“新圈地运动”。传统农民、农业、土地的未来在哪里?谁还能深情赞美“成长的土地”?影片里众多到城市抗议的愤怒的农民呈现出这不是一个桃园、一个乡村的危机,而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脸庞,村庄》《阿尔卡拉斯》中的乡村被弃置的荒凉惨败镜像就是全球乡村的现在及未来命运的缩影。
乡村危机不仅在欧美发达国家较为严重,在现代化、城市化急剧发展的中国也非常明显。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以极为悲痛的方式告诉我们:梁鸿上学的梁庄小学,今天已经蜕变为梁庄养猪场;乡村很多房屋坍塌,即使新建房屋也是少人居住,人口老龄化极为严重。笔者2025年回到山东莒县老家,看见周围数个村庄招收儿童入学的片区中心小学因为收生太少撤销办学点,而集中到乡镇中心小学办学。而这绝不是个例。乡村里没有常驻的孩子,仅有的适龄儿童也集中到县城或乡镇上学。千百年来,我们常说的生于斯、长于斯而终将老于斯的故乡,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再是生命最初的血地,更难以成为“长于斯”的家乡了。我们常说的“故乡情感”、乡愁何以建立?!梁鸿在《出梁庄记》中记载了那些曾在梁庄长大而常年在外打拼的梁庄人,每当谈起故乡,就两眼放光,一下子唤起了思乡的情感。但是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二代农民工”却是一脸茫然。融不进的城,回不去的乡:而对于二代农民工而言,从情感深处讲,他们或许根本就不认同父辈的故乡,认为那是你们的故乡,我们是没有故乡的一代。这才是当代中国进城农民的深层情感困境。正是基于这个问题,梁鸿提出了乡村之于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心灵情感结构的重要性:“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事实上,乡村之于中国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生活的空间,而是关系着一个人生死依恋的生命情感维系、一个族群的根脉传承乃至关系着民族国家共同体情感内核建构的根本性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借鉴与学习,而且体现了从根脉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度。这既是对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的当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是从历史、文化、情感的源头来铸牢以乡愁为内核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情感共同体的根本性战略举措。基于此,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就是对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计划的有力支持,是以乡村文化为精神内核的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现实实践的审美书写。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乡土文学就出现了一些较为优秀的乡村审美书写,特别是一些对千年中国乡村文化书写的文学作品。新时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学书写迎来了一个创作新浪潮,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涌现出来。徐则臣、杨志军、乔叶、付秀莹、盛可以、陈彦、陈涛、魏思孝、蔡崇达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展示新时代中国的乡村巨变、危机与新的希望。从鲁迅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叙述的情感逻辑,即从乡村到城市的叙述逻辑与情感内核,在新时代语境下有了新的、质的变化:已经从乡村到城市,延展为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世界上去的新的审美空间和情感逻辑。“到世界去”是徐则臣《耶路撒冷》小说中的主题之一。而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与赵德发的《人类世》则指向了更为辽远的宇宙星空与远古时代,是以乡村为叙述基点和情感内核的更为辽阔的“远方世界”。
不认识乡村,何以认识过去之中国?不认识乡村,何以认识今日之中国?不认识乡村,何以思考未来之中国?这就是我们要保卫乡村的最大理由和根本目的。作为中国千百年来一直不断生长、延续和滋养中国人心灵、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乡村根性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族群、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深厚的历史、文化、心灵、审美、哲学等价值意义。认识到乡村之于中国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和根本意义,我们就要毫不犹豫排除万难来保卫乡村、捍卫乡村,创造性传承千年乡村根性文化。
而在众多保卫乡村的路径中,书写乡村、以审美的方式来记录、传承和创造乡土文学,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路径。经历千百年发展、被千百年中国文学史所吟咏、为祖祖辈辈中国人生活过和无数遍萦绕于心的乡村,已经被锤炼、凝结、铸就为一种看不见的而又无处不在、时时发挥作用的润滑中国社会结构与滋养中国人心灵的乡村精神。乡村精神就是中国乡村根性文化的内核所在。而这种乡村精神正是借助于乡土文学作品的审美感染力而获得更为久远、辽阔、深刻、动人的精神力量和情绪价值,成为人类情感共振的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意识。在新时代语境下,以乡村精神为内核的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应该在文学艺术的审美建构下进一步发展为一种适应人类文明新发展阶段的新乡村现代性价值理念,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具有哲学世界观意义的精神指导与价值引领,即以新时代乡土文学来丰富乡村精神内涵,“创造新乡村”来保卫乡村。新时代乡土文学应该在延续千年中国乡村书写精神血脉的基础上,继承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乡土文学叙述传统和审美经验,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建构乡村空间的现代性价值:
“欸乃一声山水绿”“谁不说俺家乡好”。每一个乡村都有着独特的物质性风土,有着属于“一方水土”的泥气息、土滋味,有着村庄与周围山山水水、草木虫鱼鸟融一起的自然之风景。刘醒龙在《上上长江》阐述长江以南的“江南风景”的内在精神特性。沈念的《大湖消息》传递出鄱阳湖自然与人之间的精神讯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讲述了东北边地鄂温克族居住部落的大自然生态,创造出人与万物交融的“复魅”新自然空间。而新时代乡村书写,要以人类生态文明文化的新视野,来认识、描绘和建构具有生态文化视域下村庄自然万物的外在风景及其内在精神,重构乡村自然之魅,推进人与自然生命主体间交往,从而让新时代乡村成为乡民安放灵魂、慰藉乡愁的“诗意栖居”之地。新时代乡村书写亟需写出具有自然风景及其内在魅力的“新乡村风景”,创造出新乡村生态。
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历史。笔者所在山东莒县龙山褚家庄村跟附近很多村庄都是明清之际迁移而来的,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每年回老家,除夕前我都会跟家族长辈、兄弟、侄孙们一起给祖先上坟。每次上坟都是从第一代老祖的坟头开始。伴随鞭炮声磕完头后,长辈都会介绍每个坟头的来历,讲述几代祖先创业的故事。尤其是到众多祖先长眠的“老林”墓地,鞭炮声愈加震耳欲聋,田野里升起一阵阵青烟。天南海北的家族成员此时此刻汇聚一起,共同完成每年一度的祭祀仪式,一次次体认着家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地域、情感的心理认同和血脉传承。这正是无数中国乡村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生命仪式和精神时刻。毫无疑问,无论是遥远的过去历史,还是近代的种族繁衍,村庄都承载着乡土中国一个个家族血脉传承的生命史和精神史。但是,对于这些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乡村历史的文学书写是较为缺失的、不够深入的;而具有家族史、文化史意义的乡村志、乡村人文心灵史更是极为匮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乡土文学,需要以一种基于人类乡村历史文明的维度来思考和建构,进一步书写和夯实乡土中国的地方史、国族史、生命情感史。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就是一部以乡村为核心支点的汉藏几代人交融扶持的百年中国藏族乡村地方史、心灵史。
千百年来,以乡村为核心支点的中国乡村根性文化发展出了尽善尽美等伦理文化追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有余庆”等春节对联贴遍了众多中国乡村人家的大门。忠厚、诗书、向阳、积善本身就是千年中国乡村耕读文化的产物,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土地伦理相吻合,有着一种诗意、阳光、善良、积极、向上的伦理文化意蕴与精神追求。这也恰恰是乡村精神里面具有积极性、现代性和未来增长性的核心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现代文明体系所需要的可以传承、生长、拓展的根性文化内容。
事实上,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书写已经自觉不自觉涉及这一乡村根性伦理文化主体。贾平凹的《古炉》写到了给人“说病”的乡村文化,以心灵之善来祛除人心中的仇恨与贪念,医治“心病”,体现一种乡村“善文化”的建构。张炜的《古船》《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对乡村儒家文化伦理正义的思辨,倡导“大善”“长生”和对“恶”的救赎。赵德发的《君子梦》《经山海》分别对中国乡村千年“君子文化”与“楷模文化”进行审美书写和当代激活,都展示了中国当代作家对千百年中国乡村文化的历史挖掘、精神建构和可贵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而这种向上、向善、慎独、谦卑、勤劳、进取的乡村精神及其伦理文化意蕴,恰恰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是祛除焦虑、不安、躺平、佛系、断亲、“失心疯”等时代“心病”的乡村“良药”。在急剧变迁的加速度社会中,来自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的“乡村精神”及其追求向上、向阳、善美的伦理文化显得尤为重要,是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不能缺失的伦理建构和文化传承,并以此转化出新乡村伦理文化,创造出既善又美的新时代新乡村。
乡村之所以是乡村,是因为有农民的存在,因为有着乡村精神的美丽心灵的存在。有人,才有乡村,才有乡村精神。一个个乡村就是千百年来农民灵魂的栖息地。因此,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核心和关键就是要塑造具有新时代乡村精神的新农民典型形象。有了新时代农民形象,乡村就有了灵魂,乡村精神就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精神主体。陈涛的《在群山之间》以非虚构的形式书写“”的扶贫经历,讲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如何融入乡村、重新发现自己的心灵成长史。“你今天过得好吗?”蔡崇达的小说《草民》中讲述了这样一位名叫“曹操”的乡民:他每天穿街走巷一边卖杂鱼,一边问候每一户乡邻。“明天会好的”,曹操就这样安慰着“我”这样说“不好”的孩子。小说以“成佛了”来讲述东石镇乡民对“曹操”功德的纪念及其形象建构。“在完成《草民》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书写构成故乡的所有人了,仿佛重新'生'下了自己的、他人的故乡,和它达成了完全和解。”正如蔡崇达所言,乡村书写就是“生”下故乡,创造不朽的乡村。
“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时至今日,梁漱溟的话依然振聋发聩。梁漱溟认为重建中国文化必须从乡村产生。乡村是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必须立足于中国原有的基础,新时代中国的现代文化要从“老树”上发出来,从“老道理”讲起。与此呼应的是,早在1920年代,章士钊就提出“农村立国”,米迪刚、王鸿一提出“村治”“村本政治”等思想。为了实现这一文化理想宏愿,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不仅号召到农村中区,到民间中去,而且身体力行以“与农民同心之心”推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大众的结合。这在新时代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大声呼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对于新时代中国作家而言,要积极、勇敢、以使命担当的精神书写乡村、记忆乡村、创造乡村、保卫乡村。而更为严峻的是,谁来书写千年根性文化?21世纪人类在人工智能新文化语境下,谁还能熟悉乡村文化,熟悉乡村生活?极为残酷的事实是,昔日的乡村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生产技艺及其乡村文化体验,都已经渐渐进入乡村记忆博物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日趋颠覆了昔日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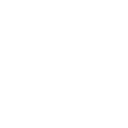

@HASHKFK